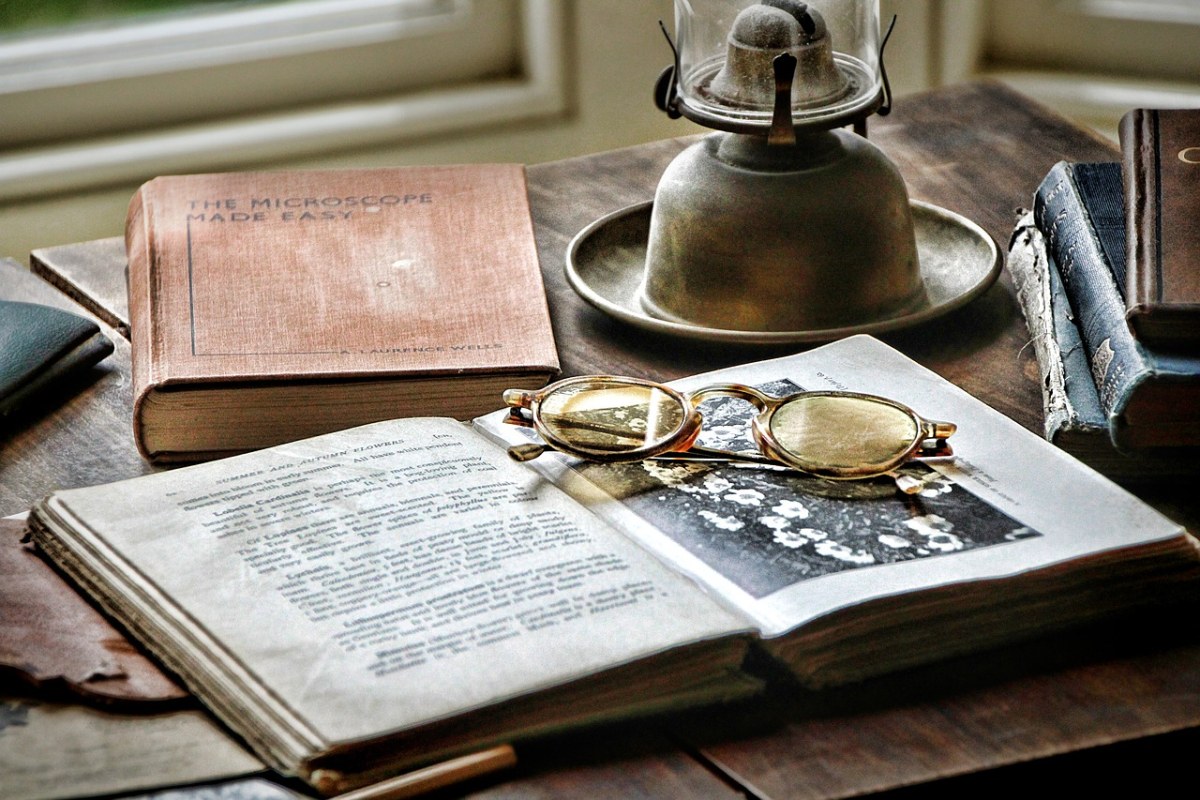虚假陈述证券民事案件的争议焦点
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争议焦点:
(一)虚假陈述所涉事项是否属于重大事件,即上市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及考量标准根据
1. 以证监会或刑事判决书为准,如上市公司的行为已经被证监会处罚或者被法院认定属于刑事犯罪,法院会以行政处罚书或判决书的内容中认为上市公司该行为已属于重大事件来认定为虚假陈述。
2. 考量违法行为对投资决定的可能性影响,是否重大的衡量指标可以通过违法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来判断,比如连续多个跌停板。
(二)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基准日如何确定
1. 虚假陈述实施日的认定
(1)积极虚假陈述行为:常见于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诉。该类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是该陈述作出之日,不是陈述的内容被作出决定之日。在“佛山照明”案,法院认为“其佛山照明发布增资行为的公告,但未在公告中披露该增资为关联交易之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而非佛山照明董事会作出增资决定之日。
(2)消极虚假陈述行为:常见于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等行为。如上市公司消极不履行披露义务,则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为信息披露法定期限的截止日。在“多伦股份(鲜言案)”中,上海一中院认为:“鉴于鲜言的不正当披露行为性质上属于消极虚假陈述,故该虚假陈述实施日的确定取决于信息披露的法定期限,即法定期限的最后一个日期应当为消极虚假陈述的实施日。
(3)如是存在一系列虚假陈述行为,法院会认定多个虚假陈述之间具有关联性和持续性,应当以首次作出虚假陈述之日为虚假陈述实施日。
2. 虚假陈述揭露日与更正日认定
虚假陈述揭露日,是指陈述在全国范围发行或播放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上首次被公开揭露之日。法院在实际认定时,一认定标准。鉴于证监会的职能及权威性,其立案调查的公告发布以后,足以说明被调查的股票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对于理性的投资者,已经起到了充分的风险提示作用,具有高度的警示性,足以影响投资决策。”
另,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揭露虚假陈述的公告或决定时,应当以第一次发布公告之日为虚假陈述揭露日。但也存在例外,若行政处罚为对一系列连续虚假陈述行为的概括处罚,则以第一次披露虚假陈述行为之日为虚假陈述行为揭露日;若行政潍坊亚星公司两次发布的山东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内容均为潍坊亚星公司存在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财务核算存在问题等,故被上诉人潍坊亚星公司的虚管措施公告是对潍坊亚星公司存在的虚假陈述行为进一步的披露,不应认为是另外的揭露日。
虚假陈述更正日是指虚假陈述行为人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自行公告更正虚假陈述并按照规定履行停牌手续之日。福州中院在“欣泰电气”案中指出“欣泰电气于2015年11月27日发布《关于对以前年度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与追溯调整的公告》,首次对外公开了公司在2011-2014年期间相关财务报表中的会计差错并自行予以更正,该更正公告所揭露的虚假陈述内容即系证监会此后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所认定的欣泰电气虚假陈述的内容,故欣泰电气的上述更正行为符合《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关于更正日的规定,本院对被告兴业证券关于2015年11月27日为第一个更正日的诉讼理由予以采信。”
3. 基准日的认定
(1)揭露日或者更正日起,至被虚假陈述影响的证券累计成交量达到其可流通部分100%之日。但通过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的证券成交量不予计算。此条指当股票的可流通的成交量达到100%时,可认为股票基本摆脱了虚假陈述的影响。
(2)按前项规定在开庭审理前尚不能确定的,则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后第30个交易日为基准日。
(3)已经退出证券交易市场的,以摘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
(4)已经停止证券交易的,可以停牌日前一交易日为基准日;恢复交易的,可以本条第(一)项规定确定基准日。
(三)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从中小投资者角度而言,无须证明其是因为信赖了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才作出投资决策,只要证明其在相应的时间点进行了涉案证券的买入和卖出并造成了损失等相关基础事实,即可推定原告的损失与被告的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其次,要考虑虚假陈述行为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四)项中的否定情形,即抗辩事由: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其中证券市场系统风险通常是指由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导致的证券市场的整体性风险。北京市一中院认为“无论是系统风险还是其他因素,均应是指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的风险因素、对证券市场所有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不能控制,是整个市场或者市场某个领域的所有参与者所共同面临的,投资人亦无法通过分散投资加以消除,因而投资者发生的该部分损失不应由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
目前认定属于系统风险需满足的条件如下:
(1)证券市场主体共同面临的,对证券市场产生普遍影响;
(2)无法为个别企业或行业所控制;
(3)投资者无法通过分散投资消除。
认定属于系统风险或其他风险的举证责任属于被告,即上市公司/发行人。引发系统风险的事由包括金融政策和突发性政治事件。比如汇率利率的变动、通货膨胀或货币贬值等属于金融政策;像2008年汶川地震、2008年次贷危机等属于突发性政治事件。即该发生的事由对证券市场股票的涨跌发挥了普遍且重要的影响。法院在实际审理中,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的大盘指数、行业指数以及同类具有代表性的个股价格走势的一致性来判断这种普遍重大影响的存在。
系统风险的计算方法包括酌情确定法;时间范围排除法及比例计算法。其中比例计算法包括指数计算法和指数个股比较法,本文暂不赘述。
(四)经济损失应如何计算
投资者的经济损失范围包括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印花税和资金利息等。其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为投资差额损失。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的若干规定》(下文简称“若干规定”)中第31条和第32条规定是计算买入均价(买入总价/买入总股数)与卖出均价(卖出总价/卖出总股数)/基准价(揭露日/更正日至基准日期间每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之差(差价),则总差额损失=差价*持有股票数量。以上情况是最高院仅设定为投资者在实施日之揭露日/更正日期间买入上市公司股票,仅在揭露日/更正日或基准日之后卖出或继续持有,并未包括投资者在此期间多次买入卖出的情况。法院在面对多次买入卖出情况,不同的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会采用不同的算法:
实际成本法:在汪雅洪与钱永耀、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一案中,北京是一中院提出若干规定所指的买入证券平均价格是指投资人买入证券的成本,因此投资人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存在多次买进卖出的情况时,其在此期间卖出股票收回的相应资金,属于投资人提前收回的投资成本,应在总投资成本中予以扣除[7]。即买入证券平均价格为在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以每次买进价格和数量计算出投资人买进股票总成本,减去投资人此期间所有已卖出股票收回资金的余额,除以投资人尚持有股票数量。
普通加权平均法:投资人平均买入价格的计算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投资人所买入股票的总金额除以买入总股数的方法,而对于投资人在揭露日前卖出的股数,不论是亏损或获益,认定为正常的商业风险,不予评价。卖出平均价亦用此法。在“海润光伏”案中,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即认可该计算方式:“郝萌在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就案涉股票存在多笔买卖,且并不能够一一对应,据此,一审法院以实施日至揭露日期间买入的股票总金额除以该期间内买入股票总数量的方式计算买入平均价,合法适当。[8]”该计算方式简单明了,但无法剔除投资人的正常投资交易损失,因为该部分投资交易损失与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移动加权平均法:计算投资人买入均价时,将投资人每笔买入与下一笔买入进行加权计算,将得出的结果再与下一笔买入进行加权计算,如此循环,直至计算至最后一笔买入;卖出平均价亦采用此法。该方法是兴业证券在“欣泰电气”案中发布《关于设立欣泰电气欺诈发行先行赔付专项基金的公告》中提出,在与投资者的诉讼中主张以该方法计算,福州中院采纳了该计算方法[9]。相比普通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可避免将正常投资损失计入虚假陈述引发的损失,虽其计算过程更为复杂,计算结果也更接近客观真实。
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即假定在证券卖出时,投资人购买在先的证券,卖出时先行退出,投资人购买在后的证券,卖出时在后退出,投资人最先卖出的股票推定为其最先买入的股票,两者进行冲抵,将未冲抵的买入股票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具有因果关系的相关证券平均买入价[10]。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比如“佛山照明”案,“紫鑫药业”案,“恒天海龙”案等,法院直接指出适用先进先出加权平均法,尤其时“多伦股份”(鲜言案)中上海市一中院对“先进先出”进行明确阐述:“对于揭露日至基准日期间存在买入和卖出情形的,对于卖出的系揭露日之前持有还是之后买入的股票,根据“先入先出法”,应当对应揭露日之前持有的股票,直至将卖出股票冲抵完毕或将揭露日之前股票冲抵完毕,卖出股票的卖出均价应当为实际卖出总价除以实际卖出数量(卖出数量小于之前持有数量)或揭露日之前持有股票数量(卖出数量大于之前持有数量)得出。”
综上所述,随着国内经济形势严峻、证券市场的波动加剧和证券监管的趋严,证券市场违约和欺诈事件暴增,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处罚逐年增多,与证券相关的诉讼及仲裁等争议解决案件的增加。对投资者而言,会爆发更多索赔机会;对上市公司或发行人而言,需更谨慎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来源:网络
汇点广场1栋A1103号。
【版权声明】:图文转载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供学习参考之用,禁止用于商业用途,如有异议,请联系。
忠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