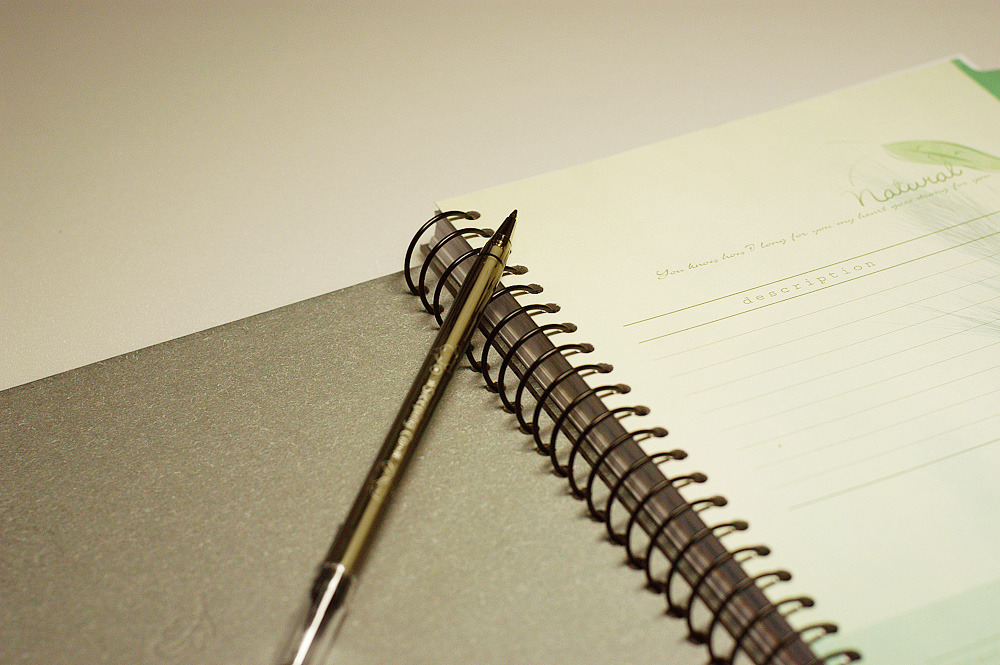新司法解释扩大了适用范围,未保留旧司法解释中排除协议转让、非公开发行等“面对面交易”的反面规定。“行为发生地”即证券交易场所成为识别新司法解释适用范围的单一标准,带有私募性质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也被纳入新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但是,新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银行间债券市场与非公开发行股票是否受到《证券法》及司法解释的调整,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均存在争议。
(一)全国首例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宣判,首次认定银行间债券市场应当适用《证券法》及新司法解释
2022年12月30日,全国首例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北京金融法院1号案)在北京金融法院宣判,法院通过承认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地位,认定其应受《证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调整。[2]在该案中,北京金融法院认为:“银行间债券市场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债券发行与交易市场。申请在银行间市场发行交易的债券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中介机构来自全国各地,银行间市场债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结算等各项机制均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基于此,银行间债券市场应属于《证券法》规定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银行间债券的发行和交易,属于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依法应当适用《证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扩张性解释“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本案为适用范围的划定提供了新的方法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在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另一起银行间债券市场虚假陈述案“康得债案”中,法院并未以《证券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为审理依据。在该案中,法院认定债券中介服务机构责任实际上依据的是《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下简称《债券座谈会纪要》)的第29至第31条,只是“参照”了新司法解释的精神;而且,在认定债券承销机构的责任时,法院未直接对其适用过错推定规则和连带责任规则。[3]可见,对于应否将新司法解释适用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虚假陈述案件,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北京金融法院1号案的认定,也向理论与实务界释放了新的信号。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能否适用新司法解释仍存争议
旧司法解释时代,协议转让、非公开发行等“面对面”交易均被排除适用。在新司法解释删去除外规定、有意扩大适用范围后,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尤其是定向增发能否适用新司法解释,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统一观点。
1.有裁判认为,新三板市场中因定向增发引起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应当适用新司法解释,进而应根据新司法解释确定管辖。
在“蓝天瑞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相关规定,发行证券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两种形式,本案某教育公司向隋某、王某、王某、刘某、刘某、由某、王某七人定向发行股票属于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形式,吴某则系通过证券市场购买某技术公司股票,故隋某等八人均属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因此,本案属于《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的情形,应适用《若干规定》确定案件管辖权。”[4]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发行人是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市的公司。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因证券交易所的流动性更高、影响范围更广,故在中因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起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亦应根据新司法解释确定管辖。
2.亦有裁判认为,定向增发引起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不可适用新司法解释,尤其不应适用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在“罗平锌电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从交易场所上来看,通过签订《认购协议》的方式购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属于在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市场以外进行的交易,不属于新司法解释的调整范围。[5]这一裁判思路与旧司法解释第3条第2项的规定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案的相关串案中,出现了混用新、旧司法解释的情况,部分裁定在新司法解释已经出台的情况下,仍引用旧司法解释,存在明显的错误。如,在(2022)云民终542号民事裁定书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径直以旧司法解释第3条第2项为法律依据,将非公开发行股票排除出《证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
无独有偶,有裁判明确表示,定向增发的投资者是特定的,不满足欺诈市场理论的前提,不应受到《证券法》及司法解释中特殊归责原则的保护。2022年8月5日,上海金融法院对全国首例新三板市场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责任纠纷作出一审宣判,认为新三板市场定增投资者索赔的案件存在特殊性,不应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上海金融法院认为:“证券侵权中依据欺诈市场理论、旨在保护不特定投资者合法权益而确立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对于新三板定向增发投资者并不适用。原告系以‘面对面’签订认购协议方式参与投资,应对行为人实施的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与其遭受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6]
3.总的来看,对于如管辖、三日一价等程序性、技术性的规则,裁判观点较为统一,多承认非公开发行股票亦可适用新司法解释。[7]对于涉及投资者倾向性保护的特殊归责原则等,司法实践中仍存争议:受旧司法解释的影响,部分裁判仍持保守态度,认为不应适用;在新司法解释明确删去旧司法解释第3条的限制后,未来的裁判观点可能会发生转向。
对新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最高法院民二庭的法官曾撰文解释道:“原解释将证券类型限定为股票、将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的做法,难以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并明确“在证券发行市场,发行人实施虚假陈述行为致使投资者认购证券的,因发行人与投资者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无论相关证券的发行是公开发行还是私募,都构成合同一方当事人(发行人)对相对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投资者难以通过撤销合同的方式获得救济……基于上述考虑,《虚假陈述若干规定》将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统一称之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一体化进行规范。”[8]事实上,对于股票而言,无论是公开发行还是非公开发行,只要投资者系以公开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即符合“市场欺诈理论”的假设前提,理应受到新司法解释的保护。虽然目前缺少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中适用新司法解释实体规则的案例,但最高法院在前文中表达的观点,可能会引导司法实践发生新的转向。